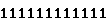加群主威: zx803011或zx803055(一塊一分四川川嘛血戰)(一元一分紅中癩子爆炸碼)手機app俱樂部里打,群內結算加不上微信就加QQ:2521077636如果添加頻繁就換一個加
26、孟子曰:不得乎親,不可以為人;不順乎親,不可以為
莊生曉夢迷蝴蝶,望帝春心托杜鵑
教授們帶給我的真的是太多太多,屬于咱們的回顧,我要把她們藏在內心,將它們形成陳年佳釀
咱們見證了爾等的開銷,咱們也懂了爾等的功夫表,都說衡水的弟子難,可我感觸爾等比咱們更難,幼嫩的肩膀撐起了太多太多
縱然咱們是冰碴是頑石,也早已被爾等和緩的手暖化了
此時現在我想輕輕的對爾等說:教授,我愛爾等
“一個造就新生命的機遇”——于是我明白了這句話的涵義
/> 春天波爾卡 □陳元武 我在春天接到的書信,封箋在一片樹葉里
(托馬斯·哈代) 我想像著堅冰被春風切開并且吹融的情形,這樣的機會還真是不多
在我生活的這個地方,十六年來總共下了四場雪,并且有兩次是連續的降雪,形成結冰
但總是在離春天還十分遙遠的時候就消融得無影無蹤了,那時我二十三歲,剛從大學嗶業半年多
我住在單位的單身樓靠東邊的單元,從窗口望下去是洗衣房和一排水龍頭的盥洗池
靠左邊的窗外是一棵懸鈴木,在冬天落光了葉子,許多刺果干在枝梢上,像被遺棄的花朵一樣,在寒風凜冽中無助地搖晃著
樹皮綻裂開,一層層的老皮干縮撓曲并從樹桿上剝離,欲掉不掉地掛在那里,里頭是灰白色的新皮露出來,我想到了傷疤這樣的字眼,那是樹的新鮮的疤痕,連結的痂皮還未脫落
那時候,經常看見一個老太太在那里撿泔水桶里的剩饅頭和飯團,她微微佝僂著背,頭上套著一個紅色的毛衣袖口改成的風帽,她偶爾抬起頭來,朝四周打量一下
她的臉是灰黃色的,而且她的左腕上有個明顯的刀疤,灰青色的
她伸手去樹上扒干樹皮的時候,左腕就露出一截,我看得很清楚
她用樹皮來擓泔水桶里的稀料,然后裝進她的泔水桶里
她離去的時候,身體有點費勁,估計是腿腳有啥毛病,桶拎在手中,身體一左一右地搖晃著,像個跛子
懸鈴木的刺果在白天的時候會突然炸開,里頭的絨毛狀籽實就像蒲公英一樣四下飄散,直飄進窗口,有時不小心鉆進鼻孔,癢得妨不住很響亮地打個噴嚏:啊――嚏――!嚇得老太太渾身一悚,驚諤地回頭張望
春天還很遙遠,懸鈴木的枝梢的芽苞還是那個樣子,密密麻麻地排列在赤裸裸的枝梢上,像甲蟲
冬天的陽光很溫暖很誘人,陽臺上和房內的旮旯總是躲藏著一些聰明的昆蟲比如臭大姐,這種模樣怪異并且渾身惡臭的昆蟲總是喜歡與人相雜而棲,它們在陽光的刺激下活動了起來,緩緩地爬出來,四肢極緩慢地伸縮試探,身上有著細小星斑的臭大姐竟然有個女性的名字,而且還是尊稱,讓我莫名其妙
它們像烏龜一樣緩緩地往窗外爬去,我不敢用手去碰,也不敢用拖鞋拍死它們
窗外的寒風總是和它們一樣討厭,不時地襲擊進來,當我在方桌旁看書或寫字的時候,一陣風沙突如其來地撲到臉上,迷住了眼睛,打翻了鎮紙的墨水瓶……那一次真的下雪了,同室的小郭子說這樣的天氣肯定下雪,我還不相信地說:不可能,你沒看見臭大姐都開始爬出去了嗎?太陽這么溫暖,雪從何來?可是當天下午真的就刮起了北風,滿天云霾,風刮在臉上像把刀子,晚上就錄錄續續地下了一陣子雪霰,噼哩啪啦地砸在窗玻璃上
幽暗的夜空像一張陰沉著的臉,雪似乎蓄謀已久地飄落下來
我們緊緊地關上窗扉,插上插銷,怕夜里讓風吹開來
廠區的方向燈火通明,電石爐的紅色火光沖天而起,映紅了大半個山谷
那些松樹明明滅滅地閃現,天空中鉛灰色的雪遠遠地看去渾沌不清,像風揚起的粉塵
雪落下來,旋即融化了,地上凌亂不堪,濕泥、草屑、吹落的樹枝和凍死的臭大姐被腳踩來踩去,上班的人腳步匆匆,嘴里呵出白白的水汽,自行車鈴聲清脆地此起彼伏
我跨上自行車的時候,看見那個老太太又一搖一晃地朝盥洗池這邊走過來了
春天似乎很突然就來了,沒有打一聲招呼
下雪過后不久,春節前的忙碌讓我忘記了窗外發生的事情
我借了幾本書來打發8小時以外的時間,當時有許多人和我一樣喜歡看經典外國文學名著
那時還沒有普及彩電,單位的電視室里每天晚上都擠滿了人,一些人喜歡看武俠片而另一些人則不喜歡,頻道被調來換去的,根本無法看下去,宿舍里沒有電視可看,書成了最佳的消磨時間的東西
我的床頭邊擺著一摞書,一半是借來的,一半是自己多年購買的私書
那時候最經常翻看的書是《普希金詩全集》、《泰戈爾詩集》、《華茲華斯作品選》和托馬斯·哈代的《還鄉》,《還鄉》是在浙大讀書時從杭州外文書店購買的原文版影印書(當時不知道是國家盜版書),朗文公司的印刷質量真是不錯,雖然是經過縮小影印,但字依然清晰
我看了許多哈代的小說,就是喜歡《還鄉》,里頭的描寫極盡功力和富有深厚雄渾的英國文學韻味
那本書應該稱為pocket